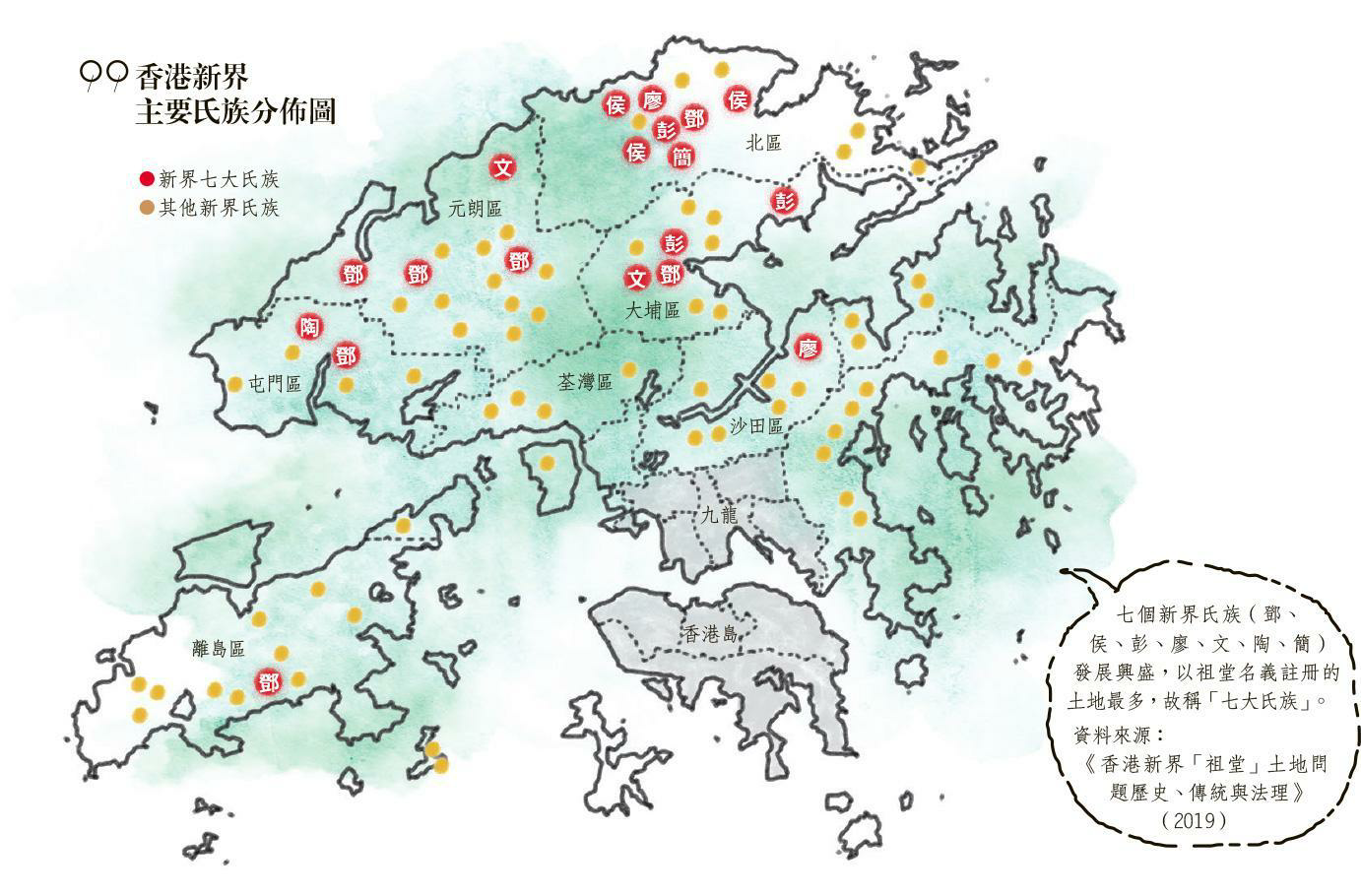2017-08-18
文︰工黨社區幹事趙恩來
業主丢空舖位、圍封通道裝修、拒開冷氣設備,這都是商場常見逼遷手法,務求令到店舖租戶無法經營,主動放棄租用舖位。別以為這些逼遷手法只在舊區重建、領展出售商場才出現,事實上食環署也會使出這類骯髒手段!
早前,食環署美其名「善用空置攤檔」,出租仍在經營中的荃景圍街市予電影製作公司搭景拍戲(*),但是拍攝期間不僅有大量器材、演員、工作人員等,阻塞街市通道,顧客不得其門而入,就連街市內唯一樓梯也被佈景圍封,居民需繞道街市附近斜路上落,街市檔主無法正常營業,苦不堪言!
荃景圍街市1990年5月2日開幕,當年政府因要安置荃灣區內路邊小販,委託荃威花園發展商「合和實業」興建市政街市,方便荃景圍附近居民購買日常所需,不假外求。街市開業之初,丁財兩旺,更有專線小巴開辦接載顧客前來購物,豬肉檔主梁先生憶述:「當時哪有人落楊屋道買餸?都來這裡!」
可惜,政府當年興建荃景圍街市,攤檔數目是取決於遷置小販需要,而非社區實際需求。假如參考當年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,規劃標準訂明每55至65戶家庭設有一個公眾街市檔位,或每1萬人設有約40至45個檔位。若以毗鄰荃威花園規劃人口約1萬來計劃,荃景圍街市有40至52個檔位便足夠,但實際上卻有241個檔位,確實遠較規劃署的標準多出一大截!
荃景圍街市當年遷置的檔販,本已是年長的路邊小販,加上2003年沙士疫情衝擊,經濟不景生意難做,不少檔主決定退休,攤檔結業交出檔位,街市出租情況每況愈下。
根據食環署提交荃景圍街市實際經營數據,2003年有131檔(出租率54%),2008年有123檔(出租率51%),均是大幅高於規劃標準。
食環署早年為要「做靚盤數」,好向公眾交代,竟把全港多個出租率偏低的公眾街市(包括荃景圍街市)劃作「準備進行攤檔整合或改善工程」,不再招標出租空置攤檔,亦會排除計算整體公眾街市出租率。結果,食環署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中,大家會發現公眾街市整體出租率逾九成,卻年年出現巨額經營虧損這樣如此荒謬窘境!
然而,荃景圍街市「準備進行攤檔整合」的計劃,一等便等了超過8年。翻查食環署資料文件,荃景圍街市對上一次公開招標空置檔位已是2009年的事!由此可見,荃景圍街市如今境況,與當年規劃不當、食環署政績考量,不無關係!
時至今日,不少人可能還在質疑出租率低,是由於荃景圍街市位置偏僻、人口老化所致。事實上,當我們嘗試翻查人口普查報告,荃威花園65歲以上長者佔13.4%,與全港長者比例(13.6%)相約。再者,長者居民較多行動不便,更加不願山長水遠、動輒半句鐘乘車往返荃灣市中心買餸購物。
與此同時,食環署管理僵化,不斷扼殺小檔主的生存空間。荃景圍街市燒味檔主眼見生意難做,曾經有意售賣燒味飯,幫補生計,但食環署回覆表示,租約訂明只准賣燒味,飯盒等熟食須在熟食檔售賣,結果居民到街市對面的超市購買燒味飯盒,不久街市內唯一的燒味檔也告結業。又有售賣有機蔬菜的檔主,食環署不讓其售賣乾貨,理由是乾貨必須在不同區域擺賣,但荃景圍街市是不會出租空置攤檔。故此,荃景圍街市門庭冷清,根本是食環署一手造成!
眼見生意一落千丈,街市檔戶選擇團結自救,可惜也敵不過食環署的官僚!荃景圍街市早於2004年開始討論重整活化計劃,主張把不同樓層攤檔遷至地下,騰空其餘兩層用作其他社區服務用途。經過8年拉鋸爭論,街市檔主、居民組織雖已達成共識,但食環署最終拒絕協助搬遷檔戶重新安裝鐵閘、水錶,活化計劃亦告吹。
翻查食環署資料,荃景圍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2012年6月開會通過擱置重整方案,當時參與決定的委員只有兩位隱形建制議員(包括林婉濱、黃偉傑)。得到當區議員支持,食環署便可理直氣壯,繼續丢空街市檔位,用時間逼使現有檔戶離開!
時至今日,荃景圍街市出租率由2008年的 51%,銳減至不足兩成。食環署更借政府顧問報告之名,決定永久關閉荃景圍街市。
根據食環署2017年4月向荃灣區議會提交的文件,聲稱顧問報告指「荃景圍街市出租率偏低是由於區內人口變化、街市位置不理想及交通不便、區內有多個街市及很多售賣同類貨品的零售店舖,對街市造成強烈競爭」。
不過,該顧問報告從未研究過荃景圍街市出租率偏低原因,且說「政府應檢視出租率低的公眾街市,例如荃景圍街市及筲箕灣街市等,評估問題的成因,以了解是因為區內街市設施供過於求、街舖競爭激烈、位置不便,還是區內發展變遷導致消費群轉變」。這樣看來,食環署確實有「講大話」之嫌,為要關閉荃景圍街市,胡亂堆砌數據!
荃景圍街市將於2018年3月1日正式關閉,檔主能夠自主決定的,只有是否接受食環署兩萬多元賠償,離開養活過無數家庭、滿載回憶的街市。當我們義正詞嚴斥責食環署堅拒招標逼死街市,我們不能忘卻地區議會早已淪陷,保皇政黨橫行無忌,不時會於關鍵時刻表態,出賣居民利益。
文章來源
***
* 按:根據維基百科,《智齒》籌備5年,在2017年開機,拍攝3個月。
星期日文學‧《智齒》:從雷米小說到鄭保瑞電影
//鄭保瑞相當用心思的影像處理,呈現出冷酷異域的香港,其中有觀塘舊區、土瓜灣美景樓的後巷,以及由荃景圍街市改裝而成的警局等等,處處都見美術指導麥國強、王慧茵的能耐。//